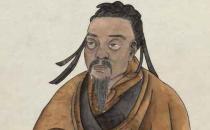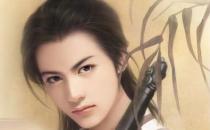揭密 康熙乾隆二帝為何經(jīng)常下江南有何隱情?
從1684年到1784年一百年的時(shí)間里,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進(jìn)行了12次大規(guī)模的南巡活動(dòng)。南巡正是帝王與江南地區(qū)社會(huì)文化的征服和被征服的過(guò)程,在這一過(guò)程中,江南地區(qū)與大清王朝的心理距離越來(lái)越近,逐漸融為一體。
12次南巡分別發(fā)生在康熙二十三年(1684)、二十八年(1689)、三十八年(1699)、四十二年(1703)、四十四年(1705)、四十六年(1707);乾隆十六年(1751)、二十二年(1757)、二十七年(1762)、三十年(1765)、四十五年(1780)、四十九年(1784)。除了康熙帝第一次南巡選擇了晚秋至初冬的寒冷時(shí)節(jié)出行外,其他數(shù)次南巡都在新年之后的正月或二月從京師啟行,抵達(dá)江浙二省的時(shí)候正是陽(yáng)春三月。江南鶯歌燕舞,繁花滿(mǎn)地,為帝王的南巡之旅增添了不少明媚的色彩。
康熙、乾隆每次從京師下江南,再叫鑾至京師,大概要三到四個(gè)月之久。這期間,水陸轉(zhuǎn)運(yùn)、物資調(diào)集、人員流動(dòng)、城市建設(shè)等頗經(jīng)周折,個(gè)中酸甜苦辣,只有當(dāng)事人了解。在當(dāng)時(shí)的條件下,皇帝下江南是一項(xiàng)浩大的工程。從北京到江浙,往返6000華里。那時(shí)沒(méi)有現(xiàn)代化的交通工具,全靠車(chē)裝船載,馬拉人扛。每次出巡,皇帝帶領(lǐng)的皇親國(guó)戚、文武百官、衛(wèi)隊(duì)侍從有兩三千人,動(dòng)用五六千匹馬,四五百輛車(chē),上千只船,需要耗費(fèi)一二百萬(wàn)兩白銀。乾隆第六次南巡時(shí)已74歲高齡了,如此長(zhǎng)途跋涉,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那為什么皇帝卻不辭辛勞連續(xù)南巡呢?
第一,上有天堂,下有蘇杭。江浙一帶是中國(guó)著名的魚(yú)米之鄉(xiāng)、豐饒之地,是清政府的主要“糧袋子”和“錢(qián)柜子”,維系著朝廷的經(jīng)濟(jì)命脈。在當(dāng)時(shí),江浙交納的糧賦占全國(guó)的38%,稅銀占全國(guó)的29%,關(guān)稅占全國(guó)的50%。當(dāng)時(shí)鹽課銀是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財(cái)政來(lái)源,鹽課銀的60%以上來(lái)自江浙。京城每年需要的400萬(wàn)石糧食,2/3從江浙漕運(yùn)進(jìn)京。如果沒(méi)有江浙的巨大財(cái)力支持,就不可能造就康乾盛世景象。每次南巡,除了確保這些正當(dāng)?shù)膰?guó)庫(kù)收入以外,皇帝和權(quán)臣還通過(guò)攤派、贊助、買(mǎi)官賣(mài)官等手段,向江浙官員和富商撈取私房銀。可以說(shuō),牢牢控制江浙,充分調(diào)用當(dāng)?shù)刎S厚的財(cái)力物力資源來(lái)支撐龐大的清朝帝國(guó),是康乾二帝下江南的首要原因。
第二,江南出才俊,自古多風(fēng)流。在清代產(chǎn)生的114名狀元中,江蘇人有49位,占到43%。設(shè)在南京的江南貢院是全國(guó)最大的科舉考場(chǎng),考生達(dá)2萬(wàn)多人。乾隆下江南的一個(gè)重要目的,就是為安邦治國(guó)發(fā)現(xiàn)人才、培植土類(lèi)、籠絡(luò)人心。在清代,江浙也是明末移民眾多的地方,反清思想廣有市場(chǎng)。乾隆南巡時(shí),一方面對(duì)文人士子采取籠絡(luò)手段,另一方面又嚴(yán)加思想控制,對(duì)持不同政見(jiàn)的知識(shí)分子嚴(yán)厲打擊,大興文字獄。
第三,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鄉(xiāng)。尤其蘇北地區(qū)是黃河、淮河、運(yùn)河交匯之處,像洪澤湖、高郵湖等一旦泛濫,淮安、揚(yáng)州、泰州等地則是一片汪洋。乾隆在《南巡記》中稱(chēng):“六巡江浙,計(jì)民生之要,莫如河工堤防,必親臨閱視。”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“歲修銀”占到全國(guó)財(cái)政支出的1110,是當(dāng)時(shí)最大的基本建設(shè)項(xiàng)目。六次南巡中,乾隆共發(fā)出數(shù)百條治水命令,實(shí)施了多項(xiàng)重大水利工程,動(dòng)用了幾千萬(wàn)兩白銀,對(duì)減少水患、保護(hù)百姓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第四,江南是“花柳繁華地,溫柔富貴鄉(xiāng)”。乾隆時(shí)期,長(zhǎng)江運(yùn)河兩岸的都市商業(yè)繁華,人氣旺盛。當(dāng)時(shí)全世界50萬(wàn)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,江蘇占據(jù)其三——南京、揚(yáng)州、蘇州。南京,人稱(chēng)“江南佳麗地,金陵帝王家”:蘇州園林,享譽(yù)天下:揚(yáng)州,更是富商云集,美景、美味一應(yīng)俱有。皇帝來(lái)到江南,看得開(kāi)心,玩得盡興,吃得可口,當(dāng)然是樂(lè)此不疲了。
第五,皇帝出巡,安全第一。江蘇沒(méi)有高山峻嶺、荒蠻之地,盜賊流寇難以藏身。特別是江蘇人稟性溫順,加上日子比較富庶,屬于那種“倉(cāng)廩實(shí)而知禮節(jié),衣食足而知榮辱”的地方。皇帝到這里,兇險(xiǎn)較少,安全可以得到保證。
康熙帝首次南巡時(shí),“三藩之亂”剛剛結(jié)束,國(guó)內(nèi)政治軍事形勢(shì)漸趨穩(wěn)定,然而朝代更替的痕跡在各地仍比較明顯,不少名勝景觀處于荒頹狀態(tài),江浙地區(qū)的社會(huì)文化心理并不穩(wěn)定,不少文人士子對(duì)明王朝仍抱有“故國(guó)之思”,對(duì)清王朝態(tài)度猶疑。而至康熙晚期及乾隆時(shí)期,清王朝的凝聚力日益增強(qiáng),江浙地區(qū)的城市景觀和社會(huì)狀況發(fā)生了很大的變化。
南巡的主要路線(xiàn)經(jīng)過(guò)清代直隸、山東、浙江、江蘇數(shù)省,浙江、江蘇二省是南巡的主要地域范圍。除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僅到蘇州就回鑾、兩位皇帝各到過(guò)一次紹興外,其他數(shù)次南巡都以杭州府為終點(diǎn)。杭州、江寧、蘇州作為江浙二省的核心城市,是皇帝駐足最多的地方;宿遷、淮安地區(qū),因察視河工的需要,也是南巡的重點(diǎn)區(qū)域;揚(yáng)州城鹽商靡集,鹽商為皇帝提供各類(lèi)聲色游樂(lè)活動(dòng),在12次南巡的旅程中,吸引了皇帝越來(lái)越多的目光。
此外,聲勢(shì)浩大的南巡活動(dòng),也給江南地區(qū)帶來(lái)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沖擊。皇帝與地方官員、士紳、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一起參與并體驗(yàn)著這種變化。在皇帝下江南的過(guò)程中,江浙地區(qū)的社會(huì)文化生活日益豐富,地方官商與帝王一起打造著前所未有的文化和視覺(jué)盛宴,其中花樣百出、創(chuàng)意無(wú)限。京師與江南溝通有無(wú),既注重南巡盛典的政治象征意義,也展示出鮮明的江南地域特色。江浙地區(qū)的城市和地域文化景觀在南巡過(guò)程中飛速成長(zhǎng),南巡中的城市和景觀建設(shè)成為國(guó)家和地方的重大基建工程,中央和地方官員對(duì)巡幸道路、行營(yíng)、行宮、歷史名勝、園林建筑進(jìn)行全面普查營(yíng)繕。江浙地區(qū)日漸富麗,面貌煥然一新。
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徜徉于江浙地區(qū)的詩(shī)意山水之間,與一些著名的江南文土結(jié)伴游玩、詩(shī)歌唱和,留下了大量的詩(shī)文作品,他們用皇家的筆觸描述詩(shī)意的江南,成為江南景觀史上一段特別的經(jīng)歷,這種影響深深地刻印在江南地區(qū)的山水文化之中,至今仍有著清晰的印記。皇帝醉心于江南山水,努力將江南文化攜帶至京師宮苑之中,造成了清中期京城皇家園林中的江南文化熱。盡管因?yàn)榈赜蚝蜌夂虻脑颍衔幕卦诰煹纳L(zhǎng)難免會(huì)有不適的狀況,但是皇帝的行為仍然增強(qiáng)了南北之間的文化交流。
康熙、乾隆南巡,是當(dāng)時(shí)的統(tǒng)治者接觸社會(huì)實(shí)際、了解風(fēng)俗民情的一種特殊的方式。他們都十分重視治理黃河,興修水利,優(yōu)禮土子,蠲免賦稅,利用南巡的機(jī)會(huì)治理水患、安定社會(huì)、了解民情、爭(zhēng)取人心,確實(shí)做了不少有益于國(guó)計(jì)民生的事情。這些舉措,對(duì)統(tǒng)治者制定治國(guó)方略、解決現(xiàn)實(shí)問(wèn)題、穩(wěn)定社會(huì)秩序、鞏固政權(quán)統(tǒng)治,是有相當(dāng)益處的。
然而,皇帝出巡有它消極的一面,那就是開(kāi)支浩繁,勞民傷財(cái)。帝王出行,總要有一定的儀式、規(guī)格,總要耗費(fèi)一些國(guó)家財(cái)力,即使是康熙南巡也存在同樣問(wèn)題。但這些花費(fèi)完全在皇帝個(gè)人的掌握之中。這樣,實(shí)際花費(fèi)的多少就因人而異。能夠自我約束的帝王,就會(huì)比較愛(ài)惜民力物力,顧念民生多艱,不隨意糜費(fèi):反之,則會(huì)大肆鋪張,任意揮霍;乃至勞民傷財(cái),損耗國(guó)家元?dú)狻?/p>
六下江南,有得有失,有利有害。通過(guò)南巡,康熙、乾隆二帝相當(dāng)清楚地了解了江南的官風(fēng)民情,又宣揚(yáng)了圣恩,對(duì)爭(zhēng)取縉紳士民、安定江浙、保護(hù)百姓的身家性命財(cái)產(chǎn)、發(fā)展生產(chǎn)、豐富文化、創(chuàng)造和延續(xù)大清全盛之勢(shì),起了積極的促進(jìn)作用。但是另一方面,開(kāi)支確實(shí)十分巨大,每次南巡,歷時(shí)數(shù)月,隨駕當(dāng)差的官兵數(shù)千名,約需用馬數(shù)千匹和船數(shù)百只,還有幾千名役夫,用掉了上百萬(wàn)銀兩,還給民間帶來(lái)了極大的騷擾。乾隆對(duì)此也很了解,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《南巡記》里,既講述了南巡成功的原因,又明確指出,不具備君主之“無(wú)欲”、扈駕人員之“守法”、官員之“奉公”、民入之“瞻覲親切”這四個(gè)條件,不可言南巡。過(guò)了十幾年,他對(duì)南巡的勞民傷財(cái)有了更深刻的認(rèn)識(shí),對(duì)軍機(jī)章京吳熊光說(shuō).“朕臨御六十年,并無(wú)失德,惟六次南巡,勞民傷財(cái),作無(wú)益,害有益,將來(lái)皇帝如南巡,而汝不阻止,必?zé)o以對(duì)聯(lián)。”也許正是因?yàn)檫@個(gè)原因,乾隆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沒(méi)有南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