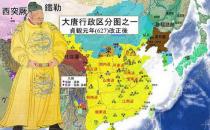甲午戰爭兵敗竟然是因為中國士兵開槍瞄不準?
近代中國的士兵接受了洋槍隊的全部裝備,也接受了洋操的訓練,連英語的口令都聽得慣熟,唯獨對于瞄準射擊,不甚了了。1920年直皖大戰,動用20多萬兵力,打下來,也就傷亡200余人,真正戰死的也就幾十人。
瞄準射擊是步兵進入火器時代的基本要領,可是這個要領,中國人掌握起來,很是費了些功夫。引進洋槍洋炮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,在這個問題上,國人一直都相當熱心而且積極,即使最保守的人士,對此也只發出過幾聲不滿的嘟囔,然后就沒了下文。鬧義和團的時候,我們的大師兄二師兄們,盡管宣稱自家可以刀槍不入,但見了洋槍洋炮,也喜歡得不得了。不過,國人,包括那些職業的士兵,對于洋槍洋炮的使用,卻一直都不見得高明。19世紀60年代,一個英國軍官來訪問中國,在他的眼里,淮軍士兵放槍的姿勢很有些奇怪。他們朝前放槍,可眼睛卻看著另一邊。裝子彈的時候,姿勢更是危險,徑直用探條搗火藥(那時還是燧發的前裝槍),自己的身體正對著探條。
過了30余年,洋槍已經從前裝變成更現代的后膛槍,而且中國軍隊也大體上跟上了技術進步的步伐,用后膛槍武裝了起來。可是,士兵們的槍法,卻進步得有限。義和團運動中,攻打外國使館的主力,其實是董福祥的正規軍,裝備很是不錯。從現存的一些老照片看,董軍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槍,而且身上橫披斜戴,掛滿了子彈。可是,據一位當時在使館的外國記者回憶,在戰斗進行期間,天空中經常彈飛如雨,卻很少能傷到人。由此看來,1萬多名董軍加上數萬義和團,幾個月打不下哪怕一個使館,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。董福祥的軍隊如此,別的中國軍隊也差不多。庚子前五年,中日甲午之戰,北洋海軍的表現大家都罵,其實人家畢竟還打了一個多少像點樣的仗。而陸軍則每仗敗北,從平壤一直退到山海關,經營多年的旅順海軍基地守不了半個月,丟棄的武器像山一樣。威海的海軍基地周圍,門戶洞開,隨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陸。當時日本軍人對中國士兵的評價是,每仗大家爭先恐后地放槍,一發接一發,等到子彈打完了,也就是中國軍隊該撤退的時候了。當年放槍不瞄準的毛病,并沒有多大的改觀。
進入民國,中國士兵腦袋后面的辮子剪了,服裝基本上跟德國普魯士軍人差不多了,建制也是軍師旅團營連排了,可不瞄準拼命放槍的喜好卻依然故我。張勛復辟,段祺瑞馬廠誓師,說是要再造共和。討逆軍里有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、曹錕的第三師、李長泰的第八師,都是北洋軍的勁旅,對手張勛只有五千辮子兵。英國《泰晤士報》記者、北京政府顧問莫里循目睹了這場戰爭,他寫道:“我從前住過的房子附近,戰火最為熾熱。那天沒有一只飛鳥能夠安全越過北京上空,因為所有的槍幾乎都是朝天發射的。攻擊的目標是張勛的公館,位于皇城內運河的旁邊,同我的舊居恰好在一條火線上。射擊約自清晨五時開始,一直持續到中午,然后逐漸減弱,斷斷續續鬧到下午三時。我的房子后面那條胡同里,大隊士兵層層排列,用機關槍向張勛公館方面發射成百萬發子彈。兩地距離約一百五十碼,可是中間隔著一道高三十英尺、厚六英尺的皇宮城墻。一發子彈也沒有打著城墻。受害者只是兩英里以外無辜的過路人。”最后,這位顧問刻毒地向中國政府建議,說他同意一個美國作家的看法,建議中國軍隊恢復使用弓箭,這樣可以少浪費不少錢,而且還能對叛亂者造成真正的威脅。
中國軍隊,自開始現代化以來,所要對付的對手,基本上是些拿著冷兵器的叛亂者。雙方碰了面,只要一通洋槍猛轟,差不多就可以將對方擊潰。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槍洋炮的對手,這套戰法就不靈了。問題在于,屢次吃過虧之后,戰法并沒有多少改善,輪到自己打內戰,雙方裝備處在同樣等級,仗也這么打。討逆之役,雙方耗費上千萬發彈藥,死傷不過幾十人。四川軍閥開始混戰的時候,居然有閑人出來觀戰,像看戲一樣。不過,打著打著,大家逐漸認真起來,終于,槍法有人講究了,畢竟不像清朝那會兒,對手凈是些大刀長矛。洋槍洋炮對著放,成者王侯,甜頭不少,所以,在競爭之下,技術自然飛升。到了蔣介石登臺的時候,他居然編了本步兵操典之類的東西,重點講士兵如何使用步槍,從心態、姿勢到槍法,尤其強調瞄準射擊。
從士兵的槍法來看,中國的現代化真是個漫長的過程,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夠了,才能有點模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