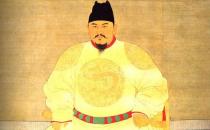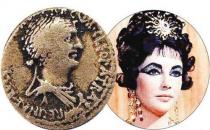中國歷史上官僚貴族化世襲化是如何被遏制的?
中國自秦漢以來,就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度,這是一個事實。官僚占有最多的社會資源,也占據著社會最多的榮耀。通俗點說,就是做官就有一切,不做官就沒有一切。但是同時,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導者,政務的操作者,國家的富強,社會的好壞,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官員的優劣,也依賴官僚制的效率。按官僚制的自身邏輯,這個制度,必須不斷地從平民中汲取新生的優秀人士,以保證官僚制的效率,維持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良性發展。所以,歷朝歷代,官員的選拔,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。但是,中國又是一個以家族為核心價值的國度,官員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關的共同體,做了官的人,有義務給自己的家族(當然包括后代)帶來好處。
兩漢實行以推薦為標志的察舉征辟選官制度,原本實行狀況良好。被推舉的人,大多是優秀人才。但是,這個制度延續一段時間之后,就出了問題。一來做高官的人,周圍的人對其子弟勢必高看一眼。即使沒有特別的托請,進入仕途的高官子弟,往往也會被人優待。高官的光環投射到自己的子弟頭上,似乎非常自然。二來,由于在制度上,高官有推薦人才的權力,對于被推薦的人而言,薦主才是真正改變他命運的人,對他有知遇之恩。待到被推薦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較大的官,也有能力推薦的時候,他們報恩的最佳方式,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薦上去,如果已經進入仕途,則在晉升方面拉一把。于是,就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局面,越是高官,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機會多,幾代累積下來,就形成了東漢末年的門閥。袁紹和袁術兩個人資質平平,但僅因為兩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,弟子門生遍天下,所以,起兵的時候,居然一時形成為最大的兩個軍閥集團。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,由于實行九品中正制,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專利。吏部選拔,只需查閱各人的牒譜便是。眾所周知,這個階段國家分裂,政治黑暗,主因就是官僚制變成了變相的世襲貴族制。
徹底改變這種局面的是科舉制度的實行。我們知道,所謂科舉制,就是考試取官。無論什么人,平民還是皇族,只要通過相關考試,就可以做官。其實,在科舉時代,對高官和皇族也有優待,不僅子弟可以上比較好的學校,而且有門蔭制度,高官子弟,可以通過門蔭,直接進入仕途。但是,由于比較嚴格的考試制度,使得這個時代形成了一種風氣,凡是不從考試出身的官員,會被認為沒有本事。花錢買官的捐班自不必說,被人看不起。而從門蔭入仕的人,也往往被人視為紈绔子弟,同樣為人輕視。風氣所及,即使是皇帝,也不大看得起這樣的人,所以,門蔭出來的人,升遷也難。在這種情景下,即使高官子弟,只要有心走仕途,往往得走科舉之途,真刀真槍考上。有人研究,自隋唐以來的科舉制,能夠保證大約有半數的及第者,出身中小士紳和平民,另外一半,多是官宦子弟。官宦子弟以門蔭為恥,使得那個時代的仕途后門開的不那么大,從而遏制了官僚貴族化世襲化的傾向。
搶官的“官二代”成為輿論詬病的權力世襲現象
現在中國的問題,首先是在于長期以來,國家并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選官制度,高考制度一度成為變相的科舉,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,干部選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徑,沒有文化的工農干部甚至還有晉升方面的優勢。即使是大學考試,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薦入學的另途,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。在大學畢業生不包分配之后,雖然實行了公務員考試制度,但到目前為止,不僅這種考試還不是國家統一考試,而且進入公務員隊伍,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徑。改革后對進入公務員隊伍實行的學歷限制,隨著“五大”畢業生(電大、職大、函大、夜大、自考)的出現,很快就形同虛設。而對海外留學生的優待,由于一些在國內考不上大學的干部子弟可以通過花錢出去留學,混一個學位,就可以回來享受優惠。 現在新生的“官二代”,有相當多的人,喜歡直接進入仕途,趁父輩尚在任上的時候,盡可能快地晉升到一定高度。這些搶官的“官二代”,形成了今天大為輿論詬病的權力世襲現象。
其次,由于官本位的緣故,在任官員掌握了社會上最多的資源,而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,依然強固。無論官員本身是否參與,一定級別的官員子弟,無論做什么,只要在這個官員的影響力之內,都不言而喻地會得到人們的照顧。如果這些官宦子弟經商,只要打出父輩的招牌,往往就會一路順風,獲得平民子弟望塵莫及的便利。在改革初期,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歡利用父輩的余蔭去下海經商,獲取經濟利益。這些人有的是官商,有的是私商,但無論官商私商,他們經商的軌跡,往往有權力的陰影。即使少數人真的如他們所說,上升或者致富,是由于自己的才干,由于大環境如是,依然難以令人口服心服。
正如常識告訴我們的那樣,“富二代”和“官二代”不見得都是壞人,“貧二代”也不見得都是好人。但是,這樣兩種明顯的不公平,加上日益惡化的官民矛盾,必然使得“官二代”成為眾矢之的。事實上,一些“官二代”瘋狂搶奪資源(包括人事資源)的行為,已經成為令人不敢恭維的官場風習的一部分,最大限度地為社會上仇官的情緒添加了燃料。跟平民相比,官員的后代,原本就有競爭的優勢,如果連競爭本身都被取消,變成赤裸裸的有權者通吃,那么,由此造成的社會危機,是不言而喻的。
政府不應強化“官本位”的傳統
雖然說,一個現代的國家,應該改變官本位的狀況,逐漸把官本位變為民本位。但是,在沒有改變之前,政府絕對不應該強化這種來自帝制時代的傳統。即使僅僅出于保證從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,出于社會穩定的需要,也必須下大力氣保障社會上升渠道的暢通。不至于讓平民的精英,因沒有上升渠道,永沉下僚,因而心生怨恨。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辦法,就是以國家之力,確立一個官員選拔的制度,并嚴格執行。同時,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晉升。
當下,存在一種相當危險的思想傾向,即在官員選拔中,引入所謂世襲的政治可靠的因素,人為地在官員選拔中,劃分出莫須有的“自己人”界限。這種傾向,如果不是某些勢力刻意為“官二代”進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勢的話,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級糊涂。這樣做,事實上在“官二代”和平民之間,劃出了一道深深的鴻溝,除了激化“官二代”和民眾的矛盾,讓仇官情緒更加高漲,沒有任何好處。
一般來說,即使在傳統王朝政治比較清明的時期,民眾的仇官情緒依然存在。人們仇官,但同時也羨官。既仇恨權力,又羨慕權力。這是官本位社會必然的伴生產品。但是,如果從根本上根絕了平民上升的渠道,讓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變成官,或者很難變成官員,那么,平民的仇官,就會達到一種無以復加的程度,變成一種非常可怕的力量。這樣的力量一旦產生,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,天下就不太平了。所以,無論如何,現在處于優勢地位的官員以及官員的子弟們,一定要清醒,千萬不能以贏家自居,肆無忌憚地通吃。在正常市場競爭條件下,通過競爭達成的贏者,想要通吃都是危險的。更何況,人們并不認為現在官場上的贏者,是真正贏者,硬要通吃,最終最危險的,其實是這些人自己。“官二代”身上的魔咒,只能用自己的行為解開,如果不思開解,麻煩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