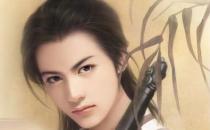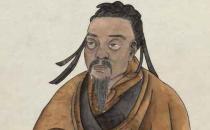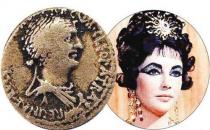誰把同治帝皇后逼上了絕路?孝哲毅皇后之死
同治帝皇后阿魯特氏是怎么死的?同治帝病逝不久,皇后阿魯特氏即死去。她的死,也是一個歷史之謎。
皇后阿魯特氏之死同她和同治帝的婚姻很有關(guān)系。同治十一年(1872)正月,慈安、慈禧兩宮皇太后醞釀撤掉垂簾,歸政同治帝。但在歸政之前,必須給時年17歲的同治帝完婚。不料,在為同治帝選擇后妃的問題上,慈安和慈禧發(fā)生了爭執(zhí)。
有清一代滿蒙人中惟一的狀元崇綺,同治帝的岳父。
慈安看中了翰林院侍講崇綺的女兒阿魯特氏。崇綺(?—1900),字文山,原蒙古正藍(lán)旗人。大學(xué)士賽尚阿之子。同治三年(1864),考中一甲一名狀元。有清一代,滿蒙人試漢文中狀元者,只有崇綺一人。他“生平端雅”,“工詩,善畫雁”。能詩善畫,多才多藝。他是一位漢文化造詣頗深的蒙族高級知識分子。阿魯特氏,“幼時即淑靜端慧。崇公每自課之,讀書十行俱下。容德甚茂,一時滿洲、蒙古右族,皆知選婚時必正位中宮”。阿魯特氏在其父親的教育下,文化水平也很高。當(dāng)時她19歲,正是好年華。慈安愛其“端莊謹(jǐn)默,動必以禮”,很想立她為后。
而慈禧卻看中了員外郎鳳秀的女兒富察氏。她還是個小姑娘,才14歲,姿性敏慧,容儀婉麗。慈禧“欲立之”。
阿魯特氏雖然容貌不如富察氏,然而“望而知為有德量者”。慈安、慈禧各有所屬,“相持不決”。這時只好召同治帝自己選定。“帝擇東后所擬定者為后”,即選擇了阿魯特氏為皇后。這就大大地得罪了慈禧。她認(rèn)為這是親生兒子有意和自己作對。但迫于當(dāng)時的形勢,她不便發(fā)作,只得暫時隱忍,便同意了立阿魯特氏為皇后,但必須定富察氏為妃子。
這樣,在同治十一年(1872)二月初三日兩宮發(fā)布懿旨,選翰林院侍講崇綺之女阿魯特氏為皇后,員外郎鳳秀之女富察氏為慧妃,知府崇齡之女赫舍哩氏為瑜嬪,前任副都統(tǒng)賽尚阿之女阿魯特氏為珣嬪。接著在二月十五日又發(fā)懿旨,大婚典禮定于本年九月十五日舉行。在這之前的七月二十六日納采禮,八月十七日大征禮。同一日,恭親王奕上一奏折,奏請大婚禮成,應(yīng)為慈安、慈禧加上徽號。兩宮太后“俯如所請”。
時光荏苒,轉(zhuǎn)眼大婚日期到了。九月十四日,同治帝身著禮服,親御太和殿,遣惇親王奕為正使、貝勒奕劻為副使,持節(jié)奉冊寶詣皇后邸,冊封阿魯特氏為皇后。派大學(xué)士文祥為正使、禮部尚書靈桂為副使,持節(jié)奉冊寶封富察氏為慧妃。九月十五日舉行大婚典禮。這一天,皇后阿魯特氏由自家邸第升鳳輿,鑾儀衛(wèi)陳儀仗車輅,鼓樂前導(dǎo),由大清中門行御道,至乾清宮降輿。同治帝身穿禮服,在坤寧宮外等候,行合巹禮。同治帝大婚便告成了。
慈禧雖然容忍了慈安和同治帝的選擇,但她對皇后阿魯特氏是不喜歡的。據(jù)說,大婚當(dāng)晚,皇后應(yīng)對,頗討同治帝歡心。同治帝讓她背誦唐詩,她竟“無一字誤”。同治帝對皇后愈加寵幸。他又見皇后氣度端凝,不茍言笑,更加敬重她。慈禧見同治帝和皇后伉儷甚篤,恩恩愛愛,很不是滋味。皇后見慈禧時,慈禧從不給她好臉色。慈禧對同治帝冷落慧妃,更是不滿,對他說:“慧妃賢慧,雖屈在妃位,宜加眷遇。皇后年少,未嫻宮中禮節(jié),宜使時時學(xué)習(xí)。帝毋得輒至中宮,致妨政務(wù)。”慈禧竟然以妨礙政務(wù)為理由不準(zhǔn)同治帝同皇后親近,讓他多親近慧妃。同治帝不敢違背慈禧的旨意,因此就很少到皇后宮中去了。但他也不愿親近慧妃。為此,他經(jīng)常獨宿在乾清宮。慈禧的干預(yù)使同治帝的婚后生活很不如意。
大婚的下一步便是同治帝親政了。
同治十二年,同治帝載淳已18歲了。
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(1873年2月23日)舉行了同治帝親政大典。
二月初八日,上諭兩宮皇太后崇加徽號為“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,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”,以示尊崇。
同治帝死,光緒帝即位,兩宮太后懿旨,封阿魯特氏為嘉順皇后。光緒元年二月二十日(1875年3月27日)嘉順皇后死去,年僅19歲。
崇綺之女、同治帝的皇后阿魯特氏。關(guān)于她的死,當(dāng)時便有傳聞,有的說是吞金,有的說是絕食。《越縵堂國事日記》說:“后即服金屑,欲自殺以殉,救之而解。”《李鴻藻先生年譜》說:“其后之崩,蓋絕食也。”《清代野史》言:“有謂阿魯特氏自傷侍疾之無狀,愿一死以殉載淳者。故當(dāng)時曾經(jīng)諭旨曰:‘上年十二月,痛經(jīng)大行皇帝龍馭上賓,毀傷過甚,遂抱沉疴,以表其殉夫之烈。’或曰,是特掩飾天下耳目之言,非實錄也。”
阿魯特氏之死確是一樁疑案。她死得很突然。冰凍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慈禧不喜歡阿魯特氏,其“不得孝欽太后歡”。據(jù)說,慈禧愛看戲,阿魯特氏陪侍左右,“演淫穢戲劇,則回首面壁不欲觀。慈禧累諭之,不從,已恨之”。阿魯特氏身邊的人勸她要同慈禧搞好關(guān)系,否則恐于己不利。阿魯特氏說:“敬則可,昵則不可。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,由大清門迎入者,非輕易能動搖也。”有人將這個話密告慈禧,慈禧“更切齒痛恨,由是有死之之心矣”。慈禧認(rèn)為,阿魯特氏是在譏諷自己不是由大清門迎入的,而是由貴人一步步升上來的。這是她所不能容忍的。以后慈禧對阿魯特氏便百般挑剔。同治帝有病,皇后不敢去侍奉,慈禧就大罵她“妖婢無夫婦情”。同治帝彌留之際,皇后哭著前往探視,并且為同治帝擦拭膿血,慈禧又大罵:“妖婢,此時爾猶狐媚,必欲死爾夫耶?”
慈禧為什么這么仇恨阿魯特氏呢?
這一方面,是因為慈禧在為同治帝選皇后時,就不喜歡她;另一方面,是因為皇后不善于逢迎。更主要的是未來的皇權(quán)之爭,這是問題的實質(zhì)。
對此野史有記載,可供我們參考。《清朝野史大觀》記道:
及帝彌留之際,后不待召,哭而往,問有遺旨否,且手為拭膿血。帝力疾書一紙與之。尚未閱竟,忽慈禧至,見后悲慘,手拭帝穢,大罵曰:“妖婢,此時爾猶狐媚,必欲死爾夫耶?皇帝與爾何物,可與我。”后不敢匿。慈禧閱迄。冷笑曰:“爾竟敢如此大膽!”立焚之。
又有記載說:
及上崩,德宗(光緒帝)立,毅皇后以與所草之遺詔不符,劇悲痛,事為那拉氏所知,亟召至,遽批其頰曰:“爾既害吾子,尚思作皇太后耶?”毅皇后跪于地,泣不止,久之,始還宮,益痛不欲生。
總之,這些記載透露出的一個重要信息,即幾乎都是圍繞一個皇權(quán)繼承問題。慈禧與嘉順之爭,決不是一般的婆媳不和,而是更深層次的皇權(quán)歸屬之爭。初出茅廬的阿魯特氏,哪里是久經(jīng)沙場的葉赫那拉氏的對手。光緒帝即位后,兩宮以太后的身份垂簾,阿魯特氏便處于十分難堪的地位。她本應(yīng)是太后,但作不了太后。作皇后吧,將來光緒帝親政后必然要立個皇后。因此,就把她逼上了死路。
其父崇綺入宮探視,分析了整個情況。他很有頭腦,向慈禧上奏如何辦,慈禧明確地說:“皇后如此悲痛,即可隨大行皇帝去罷。”據(jù)說阿魯特氏在走投無路時,曾寫一字條請命于崇綺,崇綺批了個“死”字。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。
關(guān)于她的死,《清史稿》記道:
(光緒)二年五月,御史潘孰儼因歲旱,上請更定謚號,謂:“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內(nèi),道路傳聞,或稱悲傷致疾,或云絕粒霣生,其節(jié)不彰,何以慰在天之靈?”
這個御史膽量很大,但是慈禧絕對不允許有人攻詰自己,她降旨處分了這個膽大的潘御史:“其言無據(jù),斥為謬妄,奪官。”這就壓下了不平的輿論。可以說,阿魯特氏是自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