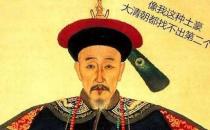屢次失敗的刺客豫讓:為何還能成春秋刺客的典范?
豫讓行刺的第一件事,就是更名改姓,偽裝成一個受過刑的人,成功進入趙襄子的宮中修整廁所。首次行刺失敗后,他不惜把漆涂滿全身,使皮膚爛得像癩瘡,把自己徹底毀容,然后假扮乞丐乞討,再次開展行刺計劃。
刺客是人類歷史中最古老的行業之一。他們的活動一般非常隱秘,行刺目的往往以圖在短時間內,讓目標人物及其相關事物遭受致命打擊。
中國職業刺客最早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,常由于政治原因,負責對目標人物進行刺殺。其行刺動機較為單純,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,因此帶有一些俠的氣息。秦以后的刺客,行刺動機多為金錢、名聲、仇恨、政治等各類原因。
漢朝史學家司馬遷著作《史記》中的《刺客列傳》,刻畫了一撥中國最早的刺客。如今被很多年輕人掛在嘴上、喜歡當玩笑話來開的那句“士為知己者死”,實際上始自于那個年代,而且在各種史料記載中,曾經真實地發生過。
持這種信念的刺客們,往往被尊為“義士”,它不僅成為刺客們行走江湖的一種執業信條,也是古代義士們最為崇信的一種氣節。
豫讓成為刺客的動因
要說中國古代刺客,不得不提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豫讓。如今廣為流傳的“士為知己者死,女為悅己者容”,就出自這名古代義士。他也被稱為“春秋戰國四大刺客”之一。
根據西漢劉向《戰國策趙策一》中記載,豫讓姓姬,是晉國俠客畢陽的孫子。他先為范氏做事,后又給中行氏做家臣,但都未受到重用,讓他覺得很是失敗。
郁郁不得志之際,豫讓遇到智伯,成為對方的家臣,而且主臣之間關系很密切,智伯對他很尊重。在他看來,智伯對他有知遇之恩。
正待境遇好轉,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際,豫讓的人生事業卻再次出現轉折。公元前475年,智伯成為晉國執政,因卿大夫趙氏拒絕獻出封地,于是他聯合魏氏、韓氏二家共同對趙氏發動“晉陽之戰”。
沒想到,到了公元前453年,當時還是晉國卿大夫之一的趙襄子派人向魏、韓陳說利害,魏氏、韓氏竟然臨陣反戈,聯合趙氏反攻智氏,智伯被趙襄子擒殺。消滅智伯以后,三家分割了他的屬地,并將晉國完全瓜分了。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“三家分晉”。其中趙襄子最痛恨智伯,還把智伯的頭蓋骨拿來作飲器。
趙襄子就是趙毋恤,嬴姓,趙氏,名毋恤(亦作無恤)。公元前475年,執晉國國政20年的趙簡子死了,其子趙無恤嗣立。后來成為了戰國時期趙國的創始人。
所謂樹倒猢猻散。主子沒了,門客豫讓無處可去,只好逃到山里。對智伯,豫讓奉其為知己,卻未能盡忠,空留一身遺憾,“士為知己者死,女為悅己者容”。對趙襄子,他暗下決心,“吾其報知氏之仇矣”。
在那個年代,“報仇”最直接的就是改行當刺客,干掉襄子。自打立下那句千古傳誦的誓言后,他的內心種下一顆頑強的種子:以后什么事都不干了,只為主公復仇。
但是行刺并不是豫讓所擅長的事情,他被后世奉為四大刺客之一,也不在于他武藝有多么高強,而是因為他對自己誓言的堅守、對忠誠的執著。
首次行刺就失敗
要殺人,首先就得改頭換面。豫讓第一件事,就是更名改姓,偽裝成一個受過刑的人,干的是打掃廁所的活兒。憑借這身臨時學來的手藝,他成功進入趙襄子的宮中修整廁所。
豫讓的想法是,打算借襄子上廁所的時候殺死他。這個算盤倒是打得好,但說實話,豫讓真不適合做刺客。第一次殺人,他就穿幫了。
雖然他如期等到襄子來上廁所,但襄子始終感覺廁所氣氛可疑,這個修整廁所的人也從未見過,心一悸動,于是抓來一問,才發現眼前這人是豫讓,衣服里面還藏著一把刀子。襄子馬上把他逮捕了。
豫讓也沒有屈服。被審問時,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動機:“欲為智伯報仇!”侍衛們都吆喝著要殺掉他,沒想到,襄子倒格外開恩。
他無比感慨地說:“他是義士,我以后謹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。況且智伯死后沒有繼承人,而他的家臣想替他報仇,這是天下的賢士啊。”在侍衛們的一片反對聲中,最后還是把豫讓放走了。那可是一個有著義士之風的年代。
不得不說一下襄子,此人生于五霸稱雄的春秋末代,卒于諸侯兼并的戰國早期。《史記》中所列趙國的襄子紀年,在位為33年(公元前457年-公元前425年),性格沉穩,頗有遠略,見識不同常人。
在趙簡子(趙鞅)的一干兒子中,趙襄子最初一點優勢都沒有,母親是從妾,又是翟人之女,所以他在諸子中名分最低,處于庶子的地位。在他小時候,甚至連趙鞅也看不上他。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,而是趙伯魯。但趙襄子從小機敏好學,膽識過人,不似諸兄紈绔,乃至多年后他贏得父親趙鞅的青睞,趙伯魯被廢掉,而他被破例立為太子。
前文提到的“智伯之怨”,實際上由來已久。趙鞅死后,晉國正卿由智伯取而代之。智伯與趙襄子曾有過多次合作,比如一同率兵包圍鄭國京師,他很瞧不起趙襄子,曾罵他“相貌丑陋,懦弱膽怯”。4年之后,再次一同討伐鄭國時,智伯還借酒醉將酒杯扔到襄子臉上。
面對這些屈辱,就連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,主動請纓要求殺掉智伯,以洗刷恥辱。但襄子的回答是:“主君之所以讓我做儲君,很重要一點,就是因為我能忍辱負重。”
現在看來,他能容忍智伯,還不能容忍一個“義士”嗎?哪怕,這是一個要殺自己的義士。
徹底毀容、毀聲再上陣
按理說,豫讓被逮個現行,又被寬厚仁慈的襄子給放掉,證明自己就不是殺人的料,理應就該收手了,心懷感恩才是。但是豫讓根本不會,他心里還揣著那句誓言:士為知己者死。
他干了一件聳人聽聞的事情,開始全面改造自己的外形:不惜把漆涂滿全身,使皮膚爛得像癩瘡。同時又剃光了胡須和眉毛,把自己徹底毀容,然后假扮乞丐乞討。
令人感慨的是,他現在這副樣子,走在大街上,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認得他了。不過,妻子說的一句話,又讓他覺得對自己的毀滅還有待升級。妻子說,“這個人長像并不像我的丈夫,可是聲音卻極像,這是怎么回事?”
沒想到,豫讓轉而就活活吞下火炭,為的是燒壞聲帶,改變自己的聲音。
就連朋友們也看不下去了,對豫讓又是可憐又是惋惜,并且還潑起了冷水:“你這種辦法很難成功,如果說你是一個志士還可以,但說你是一個明智之士就錯了。”
他們為豫讓支招:憑你的才干,如果竭盡忠誠去侍奉趙襄子,那他必然重視你和信賴你;待你得到他的信賴以后,你再實現你的復仇計劃也不遲,而且你一定能成功。
但豫讓聽了這話后,不以為然地笑了。他認為,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,為舊君主而去殺新君主,這很不齒很不道德,也是一種極端敗壞君臣大義的做法。
“今天我所以要這樣做,就是為了闡明君臣大義,并不在于是否順利報仇。”豫讓和朋友的這句對話,得以窺見他內心的真實想法:復仇的結果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復仇本身。
他說,“況且我已經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,卻又在暗中陰謀計劃刺殺人家,這就等于是對君主有二心。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為卻要這樣做,也就是為了羞愧天下后世懷有二心的人臣。”
橋上行刺再失敗,趙襄子成全一刺
盡管提前做了各種計劃,把自己也弄得面目全非,最終豫讓的算盤還是落空了。
毀容之后的豫讓提前摸清了趙襄子某天的出行時間和路線,在他要外出的那天,提前埋伏于一座橋下。這座橋如今已成名勝古跡,古典中還有記載,名曰豫讓橋,并被解釋為豫讓行刺趙襄子之處。
豫讓橋國內據傳有兩座:一座為邢臺豫讓橋,如今在河北邢臺市區內,在明朝《順德府志》中還有記載;另一處為赤橋,原名豫讓橋,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橋村,現存完好,橋為砂石砌筑,橋上勾欄圍護,橋下晉水常流,赤橋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為赤橋村。
這天,趙襄子的人馬果然行至此處。沒想到還沒到橋上,馬兒突然受驚。襄子立馬猜到是有人行刺,很可能又是豫讓。派手下人去打探,果然分毫不差。豫讓再次被拿下。兩人有一番經典對話。
顯得有些生氣的趙襄子,跟豫讓理論起來:“你不是曾經侍奉過范氏、中行氏嗎?智伯把他們都消滅了,而您不替他們報仇,反而托身為智伯的家臣。智伯已經死了,您為什么單單如此急切地為他報仇呢?”
豫讓解釋了自己的初衷,翻譯成現在的話說就是:“我侍奉范氏、中行氏,他們都把我當作一般人看待,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。至于智伯,他把我當作國士看待,所以我就像國士那樣報答他。”
偏偏趙襄子也很服這種人。但他又覺得不能再把豫讓放掉,就下令讓兵士把豫讓團團圍住。正猶豫怎么處置他,沒想到豫讓首先開口了。
豫讓知道可能生還無望,無法完成刺殺趙襄子的誓愿了。令人驚訝的是,他隨后向趙襄子提出一個荒唐的請求:請他脫下一件衣服,讓自己象征性地刺殺一下,以完成最初的誓言。
據《戰國策趙策一》記載,最終襄子還是滿足了豫讓這個要求,派人拿著自己的衣裳給豫讓。
“豫讓拔劍三躍,呼天擊之曰:吾可以下報智伯矣。遂伏劍而死。”據說,他死之日,趙國之士聞之,皆為涕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