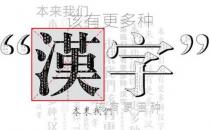三國時(shí)期曹魏書法家鐘繇在書法上的巨大成就
鐘繇,字元常,潁川長社(今河南長葛)人,生于東漢桓帝元嘉元年(151年),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(230年)。鐘繇出身于東漢望族,祖先數(shù)世均以德行著稱。曾祖父鐘皓“溫良篤慎,博學(xué)詩律,教授門生千有余人”(《三國志·魏書·鐘繇傳》引《先賢行狀》),祖父鐘迪因黨錮之禍而終身沒有做官。父親早亡,由叔父鐘瑜撫養(yǎng)成人。
鐘繇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書法成就,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據(jù)唐代張彥遠(yuǎn)《法書要錄·筆法傳授人名》說:蔡邕受于神人,而傳與崔瑗及女文姬,文姬傳之鐘繇,鐘繇傳之衛(wèi)夫人,衛(wèi)夫人傳之王羲之,王羲之傳之王獻(xiàn)之。可見,鐘繇是蔡邕書法的第二代傳人。其實(shí),鐘繇的書法藝術(shù)之所以取得巨大藝術(shù)成就,并不限于一家之學(xué)。宋代陳思《書苑菁華·秦漢魏四朝用筆法》就記述了鐘繇的書法成功經(jīng)過,說他少年時(shí)就跟隨一個(gè)叫劉勝的人學(xué)習(xí)過三年書法,后來又學(xué)習(xí)曹喜、劉德升等人的書法。因此,鐘繇與任何有成就的學(xué)者一樣,都是集前人之大成,刻苦用功,努力學(xué)習(xí)的結(jié)果。鐘繇在學(xué)習(xí)書法藝術(shù)時(shí)極為用功,有時(shí)甚至達(dá)到入迷的程度。據(jù)西晉虞喜《志林》一書載,鐘繇曾發(fā)現(xiàn)韋誕座位上有蔡邕的練筆秘訣,便求韋誕借閱給他,但因書太珍貴,韋誕沒有給他,雖經(jīng)苦求,韋誕仍然是不答應(yīng)借給他。于是鐘繇忽然情急失態(tài),捶胸頓足,以拳自擊胸口,傷痕累累,這樣大鬧三曰,終于昏蹶而奄奄一息,曹操馬上命人急救,鐘繇才太難不死,漸漸復(fù)蘇。盡管如此,韋誕仍鐵心一塊,不理不睬,鐘繇無奈,時(shí)常為此事而傷透腦筋。直到韋誕死后,鐘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書,從此書法進(jìn)步迅猛。這件事也是小說家們的虛構(gòu),韋誕比鐘繇還晚死二十余年,鐘繇怎么能去盜韋誕的摹呢?而且,鐘繇身為皇朝重臣,怎肯如此失禮?不過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鐘繇為書法的提高確實(shí)作了不懈的努力。另據(jù)《書苑菁華》記載,鐘繇臨死時(shí)把兒子鐘會(huì)叫到身邊,交給他一部書法秘術(shù),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訴鐘會(huì)。他說,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時(shí)間集中精力學(xué)習(xí)書法,主要從蔡邕的書法技巧中掌握了寫字要領(lǐng)。在學(xué)習(xí)過程中,不分白天黑夜,不論場合地點(diǎn),有空就寫,有機(jī)會(huì)就練。與人坐在一起談天,就在周圍地上練習(xí)。晚上休息,就以被子作紙張,結(jié)果時(shí)間長了被子劃了個(gè)大窟窿。見到花草樹木,蟲魚鳥獸等自然景物,就會(huì)與筆法聯(lián)系起來,有時(shí)去廁所中,竟忘記了回來。這說明了鐘繇的書法藝術(shù)確實(shí)是自己勤學(xué)苦練的結(jié)果。在苦練的同時(shí),鐘繇還十分注意向同時(shí)代人學(xué)習(xí),如經(jīng)常與曹操、邯鄲淳、韋誕、孫子荊、關(guān)枇杷等人討論用筆方法問題。鐘繇不但自我要求嚴(yán)格,對(duì)于弟子門生也同樣以嚴(yán)要求。據(jù)說鐘繇的弟子宋翼學(xué)書認(rèn)真,但成效不大,鐘繇當(dāng)面怒斥,結(jié)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見老師。最后宋翼終于學(xué)有所成,名振一時(shí)。對(duì)于兒子鐘會(huì),鐘繇也常常苦口婆心,百般勸誡,鐘會(huì)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,鐘繇、鐘會(huì)父子被人們稱為“大小鐘”。
鐘繇的書體主要是楷書、隸書和行書,南朝劉宋時(shí)人羊欣《采古未能書人名》說:“鐘有三體,一曰銘石之書,最妙者也;二曰章程書,傳秘書教小學(xué)者也;三曰行押書,相聞?wù)咭病!彼^“銘石書”,即指正楷,“章程書”即隸書(八分書),“行押書”指行書。鐘繇書法真跡到東晉時(shí)已亡佚,人們今天所見到的要么為臨摹本,要么系偽書。一般地認(rèn)為有“五表”、“六帖”、“三碑”。“五表”指《宣示表》、《薦季直表》、《賀捷表》(又叫《戎路表》)、《調(diào)元表》、《力命表》。這是現(xiàn)存鐘繇書法藝術(shù)性最高的作品,但都不是鐘繇的真跡。褚遂良《晉右軍王羲之書目》說,《宣示表》是唐代所傳王羲之臨本。因王羲之亦為書法大家,所以他臨摹鐘繇的真跡非常成功,從中可以看到鐘繇書法的情況。《宣示表》真跡據(jù)王羲之曾孫王僧虔《書錄》說:太傅《宣示》墨跡,為丞相始興(王導(dǎo))寶愛,喪亂狼狽,猶以此表置衣帶。過江后,在右軍處,右軍借王修,修死,其母以其子平生所愛納諸棺中,遂不傳。所傳者乃右軍臨本。《調(diào)元》、《力命》、《賀捷》三表,也是后人臨本,但成就亦較高。《薦季直表》可信性最強(qiáng),在唐宋時(shí)期由宮中收藏,周圍印有唐太宗李世民“貞觀”玉璽,宋徽宗趙佶“宣和”、宋高宗趙構(gòu)“紹興”,以及清乾隆“乾隆真賞”等御印,說明它曾經(jīng)由以上各帝御覽。后幾經(jīng)輾轉(zhuǎn),毀于民國十三年(1924年),今僅存其影印件。
相關(guān)文章
推薦閱讀
- 1陶淵明千古鴻文 兩晉僅一《歸去來辭》
- 2孔明借東風(fēng)打一成語 孔明燈的來歷
- 3清明上河圖中的人數(shù)是怎么估算出來的
- 4古代禮儀大揭秘 下跪是從什么時(shí)候開始的?
- 5中秋節(jié)為什么吃月餅?中秋節(jié)吃月餅的由來習(xí)俗
- 6七夕節(jié)的由來與傳說 七夕是什么時(shí)候幾月幾號(hào)
- 7中秋節(jié)的來歷和習(xí)俗 關(guān)于中秋節(jié)的傳說有哪些
- 8重陽節(jié)是幾月幾日?重陽節(jié)的來歷及傳說是
- 9臘八節(jié)是幾月幾號(hào)?臘八節(jié)的來歷及習(xí)俗是
- 10除夕的來歷與習(xí)俗是什么 古人怎么過除夕